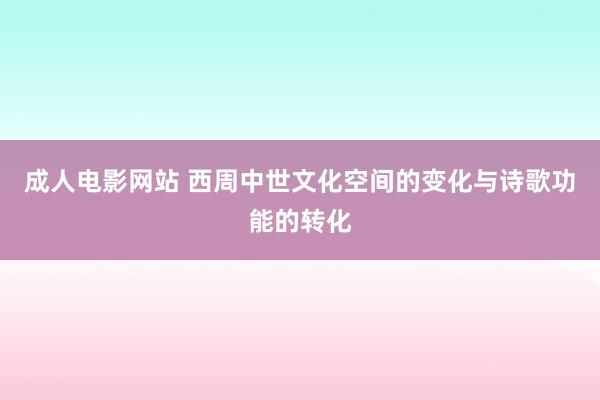论毛、郑《诗》学“正变”说之合感性 ——兼谈西周中世文化空间的变化与诗歌功能的转化 李春青 内容撮要:诗歌在西周初期的国度意志形态建构经过起到了至关垂危的作用。关联词到了西周中期,诗歌原本赖以存在的并瓦解功能的文化空间发生了垂危变化,于是诗歌原有的意志形态功能逐渐弱化,而多样新的功能随之产生并发展起来。“正变”之说原是汉儒从诗歌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对《诗经》作品进行的分类,清代以来不少学者对这一分类方法持全盘含糊作风,这是失之放纵的。 要害词:文化空间 意志形态 正变 无算乐 作家简介:李春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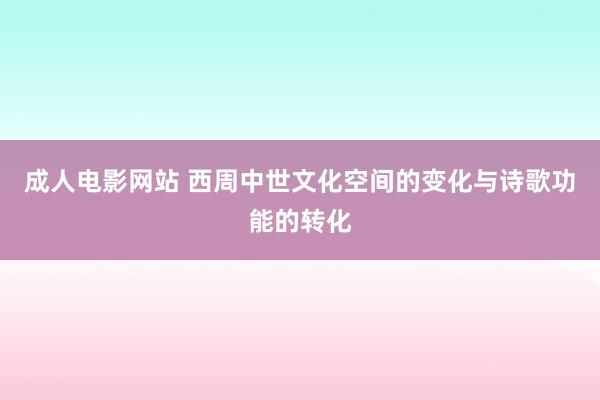
论毛、郑《诗》学“正变”说之合感性 ——兼谈西周中世文化空间的变化与诗歌功能的转化 李春青 内容撮要:诗歌在西周初期的国度意志形态建构经过起到了至关垂危的作用。关联词到了西周中期,诗歌原本赖以存在的并瓦解功能的文化空间发生了垂危变化,于是诗歌原有的意志形态功能逐渐弱化,而多样新的功能随之产生并发展起来。“正变”之说原是汉儒从诗歌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对《诗经》作品进行的分类,清代以来不少学者对这一分类方法持全盘含糊作风,这是失之放纵的。 要害词:文化空间 意志形态 正变 无算乐 作家简介:李春青,男,1955年9月生,文体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体院教授、文艺学商酌中心商酌员、博士生导师 一 西周初期周公等东说念主为了意志形态的需要创制的那些颂诗及部分大小雅之作,一朝作为乐章而且成为礼节轨制的构成部分,它们也就获取了某种安然性——在相等长的时期内这些乐章终点功能都不会被改变。这也许就是班固所谓“成康没而颂声寝”的确实原因。后世诸王,倘不对礼乐轨制作念大的更动,就必定会沿用那些周初创制的乐章。如斯久而久之,这些乐章原本的那些意志形态功能也就逐渐淡化,直至消释了。事实上,到了西周中世的昭、穆二王之后,周东说念主的统帅早已深入东说念主心,获取了胸有成竹的正当性,也不再需要用诗歌的言说方法来强化这种正当性了。班固说“成康没而颂声寝”,而郑玄《诗谱序》在“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之后即言“后王稍更陵迟,懿王……”,自成王乃至懿、夷二王之间的康、昭、穆、共四王概难受及,这是什么原因?就怕恰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一百多年间在诗乐方面莫得大的制作之故[1]。此期诗歌的具体功用大略会有改变,举例原用于祭祀大典的乐章移为他用等。但诗歌总体的意志形态功能除了逐渐削弱以外莫得任何改变。那么具有新的功能的诗歌是如何产生的呢?《毛诗序》的作家和郑玄都是颇有历史目光的东说念主,他们仍是很明晰地指出了社会政治的变化对于诗歌功能转化的决定性影响。可惜的是清代以来一些学者,非常是“古史辨”派对《诗序》和《郑谱》的不雅点完全含糊,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辨了。看他们的阐发,主若是对于《诗序》与《诗谱序》的“好意思刺”、“正变”说难以贯通,非常是对于按照期间的限定分辩“正变”的不雅点不可遴选。举例顾颉刚先生说: 汉儒愚笨到了终点,以为“政治兴衰”、“说念德优劣”、“期间迟早”、“诗篇先后”这四件事情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掀开《诗经》,看到《周南》、《召南》的“周、召”二字,以为这是了不起的两个圣相,这“风”一定是“正风”。《邶》、《鄘》、《卫》以下,莫得什么名东说念主,就料定为“变风”。他们掀开《小雅》看见《鹿鸣》等篇矞皇典丽,心想这一定是文王时作的,是“正小雅”。一直翻到《六月》,忽然看见“文武吉甫”一语,想起尹吉甫是宣王时东说念主,那么这一篇一定是宣王以后的诗了,宣王居西周之末,期间已晚,政治必衰,说念德必劣,天然是“变小雅”了。但《四月》以下很有些赞誉称善的诗,和《鹿鸣》等篇的意味是通常的,这如何办呢?于是“复古”、“伤今念念古”、“念念见正人”、“好意思宣王因以箴之”等话都加上去了。翻到《民劳》,看见内部有“无良”、“惛怓”、“寂虐”等许多坏字眼,从此以后一定是“变大雅”了[2] 因此顾先生以为“正变”之说是弥散不可竖立的。这种不雅点影响巨大,基本上为学术界所招供。举例何定生先生的不雅点就很有代表性: ……毛诗最讲欠亨处,就是以诗的世次来定“正变”的法度。他们硬性端正成王昔时者为“正诗”,懿王以后者为“变诗”。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正诗”都蚁合在文王到成王的七八十年间,而康昭以后以至共王一百多年,便连一篇都莫得,成为诗经的真空期间?康、昭期间莫得一篇“正诗”已属可怪,为什么穆、共六十余年间也连一篇“变诗”都莫得,而必比及懿王才启动“变诗”的期间呢?但就这小数,即足以证明毛诗用世次来分别“正变”之不对理了。因为三百篇即使可以用“正变”来分类,也只是个案的分类,决不可用世次来硬性分辩,一硬性分辩,便光显有主不雅的作用,不符事实了。[3] 顾颉刚与何定生先生提议的意义看上去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实则否则。用“正变”来为诗三百分类是有主不雅性的,正如任何分类、任何定名都势必有主不雅性一样。但按世次分诗之“正变”则是唯独合理的聘请。缘何见得呢?源流,不可将“正变”与“好意思刺”完全对应而论之。《诗序》、《毛传》、《郑笺》、《郑谱》都莫得说“变诗”中弥散莫得“好意思诗”。而且《小大雅谱》明确指出:“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好意思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正之次也。”这阐述“正变”之分并不是从“好意思刺”着眼的。对于“变诗”中有不少“好意思”诗这么的事实任谁都无可含糊,何况《豳风》的确大都是歌颂周公的呢!毛、郑等天然也不会睁眼说瞎话。其次,康、昭以后百余年莫得诗并不可怪,因为这个时期复旧武、成礼法,无须增删,或者说此期诗歌作为正乐之乐章的功能莫得改变。既然礼乐典礼中的一切都隐世无争、各依其序,如果莫得大的政治原因,天然是用不着、也不允许改造的。最主要的是,对于乐章创作家来说根本就莫得改变的冲动或心情。他们莫得意义去改变相沿已久的乐章。第三,正如皮锡瑞所说,后世论者不免用今天的目光看古东说念主。从功能的角度看,西周期间的所谓“诗”与后世眼中的“诗”根本就不是归拢性质的东西,应知它是礼乐轨制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用来抒写个东说念主的闲情逸致或愤慨扞拒的!轨制岂可松驰变动?轨制创立之初,周公等东说念主证据先前的文化资源聘请了“诗”这种言说体式或书写体式与“乐”一同作为礼法的构成部分,造成“诗”创作的一个蚁合时期。此期一过,“诗”就不再是一种“活的”言说体式了。它何时重新获取活力而插足东说念主们现实的政治文化空间,则有赖于历史需求的召唤。是以第四,“正变”其实恰是对诗歌应期间需求而升沉变化这一情形的准确把捏——“正诗”代表周初创制或集聚的插足了礼乐轨制系统中的那些作品;“变诗”则代表那些自后因为轨制的变化而获取全新的功能的作品。 对于“变风变雅”的说法是汉儒提议来的。《毛诗序》和郑玄《诗谱序》都以为所谓“变风变雅”是周室衰微、王纲解纽期间的产品。按郑玄的分辩,《风》[4]诗除《周南》、《召南》以外皆为“变风”;《大雅》自《民劳》之后,《小雅》自《六月》之后皆为“变雅”。这里有一个问题应予防卫。看《诗谱序》与《毛诗序》的说法,细腻正变之分的法度是期间的兴衰,海晏河清的诗是“正风正雅”,错落衰微之世的诗是“变风变雅”。关联词如何分辨一首诗究竟产于何时呢?比喻《周南》、《召南》,《毛传》、《郑笺》均以为是西周初文王期间的作品,是以以为是“正风”,关联词后代学者证据诗的内容和文辞技巧商酌发现,其中不少作品是西周末年致使东迁之后的作品。3。当代学者多招供这种不雅点。陆侃如、冯沅君著《诗史》经过考据后指出:“由此可知《二南》中不但莫得一篇可以证明是文王时诗,何况莫得一篇可以证明是西周时诗。同期可以推定的几篇却全是东周时的作品。”4这么一来,《毛诗》《郑笺》的正变之分似乎也就失去了切实的证据。对于这一情况可以这么来贯通:《二南》之诗大略并非文王时的作品,关联词其被集聚入乐的时刻应该较之其他“十三国风”为早,并被王室乐师纳入到礼乐系统之中。这类诗天然不可能像“颂”和“正雅”那样成为首要祭祀礼节的乐章,关联词却可以成为崇拜的“乡乐”、“燕乐”或“房中之乐”,从而获取“正”的地位。举例据《仪礼》的记录,在“乡饮酒礼”就有以《二南》之诗为乐章的乐次。其他“十三国风”的作品尽管也均被入乐,但都是用于“无算乐”的百戏,并无固定的用途,故而只可算是“变风”。这么“正变”的分辩照旧依据诗歌功能的历史演变而作出的。 顾炎武有一段尝引起很大争议的话很值得防卫,其云: 《钟饱读》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风》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大雅》,而谓之‘变雅’—— 《诗》之不入乐者也。”5 这也就是说,诗三百并非全部入乐,入乐者谓之“正”诗,不入乐者谓之“变”诗。全祖望则反驳说: 古未有诗而不入乐者。特宗庙朝廷祭祀燕享不必,而其属于乐府,则奏之以不雅俗例,是亦乐也。是以吴札请不雅于周乐成人电影网站,而各国之风并奏。不谓之乐而何?古者四夷之乐成人电影网站,尚陈于皇帝之庭,况各国之风乎?亭林于是乎走嘴。况变风亦概而言之,卫风之《淇澳》、郑风之《缁衣》、皆风之《鸡鸣》秦风之‘同袍’、‘同泽’,其中未曾无正声,是又不可不知也。6 顾炎武的“变”诗不入乐之说虽不可竖立,关联词他从“乐”的角度来看待正变却是有目光的。如概述顾、全二说则可以得出这么一个论断:“正”诗都是入乐的,这小数莫得疑问。“变风变雅”则即使入乐,其功能也与“正”诗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们不是那种用于祭祀、朝会、宴饮的典礼化的或者崇拜的乐舞歌辞,而是另有他用的。对于诗作为乐章的用途朱熹尝言:“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则太师所陈,以不雅俗例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1不雅朱熹之言,则《颂》与“正风”、“正雅”都是入乐的,是固定化或典礼化的歌辞,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所用之场合不同;而“变风变雅”与“正”诗的区别在于它们均不是崇拜的礼节乐章,至于是否是“太师所陈,以不雅俗例”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顾炎武还有一个创见,以为诗不应分风、雅、颂三类,而应分南、豳、雅、颂,其他十二国风则为附录2。梁启超在《诗经解题》中则将诗分为南、风、雅、颂四类,似是受到亭林的影响。他追想此四类诗的用途时说:“略以后世之体比附之,则风为民谣,南雅为乐府歌辞,颂则脚本也”3梁启超以为“风”即是“讽”,是“不歌而诵”的诗;“雅”即是“正”,是周代通行的“正乐”;“颂”即是“容”(舞容),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乐舞歌辞。这种说法同样是从功能上看“正”“变”之异同的。 非论上述诸家之说存在着如何的劣势,咱们以为其总体上是揭示出了《诗经》作品在编排上体现出的基分内类原则的。这阐述“正变”之说并非汉东说念主毫无证据的捏造,而是证据诗歌在永远使用经过中泄漏出来的功能互异而作出的合理分类。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先生也提议过很好的见解: 窃谓诗之正变,若就诗体言,则好意思者其正而刺者其变,然就诗之年代先后言,则凡诗之在前者皆正,而继起在后者皆变。诗之先起,本为颂好意思先德,故好意思者诗之正也。终点后,时易世变,诗之所为作家变,而刺多于颂,故曰诗之变,而虽其时颂好意思之诗,亦列变中也。故所谓诗之正变者,乃指诗之产生终点编制之年代先后言。凡西周成康昔时之诗皆正,其时则有好意思无刺;厉、宣以下继起之诗皆谓之变,其时则刺多于好意思良友。[5] 这是我所见过的古今对于“正变”之说最为公允、合理的解释。毛郑此说将诗的创作与期间揣度起来,其合感性是进攻置疑的。诗的当先制作、使用都是为了强化周东说念主统帅的正当性,是意志形态语言建构,理所天然是有好意思而无刺。这么的诗作为乐章永远使用于多样礼节行为之中,久而久之,成为通例,成为定制,这就是所谓“正”。自后产生或集聚来的怨刺之作与原有之诗在创作筹备、内容乃至利用上都有很大分别,乃诗之变体,故谓之“变”。 二 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正如西周初期诗歌的产生和利用是期间政治需要使然一样,自后诗歌功能的变化也同样是稳当新的政治需要的驱散。周公主办制定的封建宗法制以及相应的礼乐轨制的确起到了安然社会政治纪律与价值纪律的垂危作用,其驱散就是成、康、昭、穆百余年间的繁茂安然。史载:“成康之世,寰宇沉稳,刑措四十年不必。”[6]关联词权力的迷惑毕竟非诸侯们能够永远抵御得住的。西周以血亲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再加上严格的礼节轨制的强化,似乎造成了套严实、系统、趁火攫取的政治架构,一切权力的利用、分拨、叮咛都有澄澈的端正,因而可以隐世无争地进行了,关联词事实上却并非如斯。下列情形的出现均可视为对西周政治轨制松动的征兆: 晋侯作宫而好意思,康王使让之。 十九年,天大曀皆震,丧六师于汉。 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反。 (以上见《古本竹书编年》)鍱 炀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费杀幽公而自强,是为魏公。 (《史记·鲁周公世家》) 昭王之时,王说念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诸侯有顶牛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 ( 以上见《史记·周本纪》) 晋侯作宫室而好意思,定为越制之举,否则康王不会派东说念主去谴责他。这阐述早在康王之时,在诸侯之间不合乎礼法的行动就仍是存在了。昭王期间应是西周由盛而衰的转念点,亦然礼乐轨制由贯通而走向松动的转念点。昭王“丧六师于汉”以及“南巡不反”可以说是西周自武王以来最为首要的繁难。这么一个首要事件最大的负面效应乃是动摇了周王室在百余年间建设起来的结拜地位,天然也动摇了周王室对于诸侯的巨擘性。于是才会出现鲁国幽公之弟弑兄自强这么骇东说念主视听的事件。周王室对这个事件是如何的作风,于史无征,但弑兄的魏公并莫得受到责骂,更莫得受到应有的征伐,这示意周王室对他的篡位是默许了。这种情形阐述王室之于诸侯仍是有些尾浩劫掉了。是以《史记》说昭王之时“王说念微缺”是有史实证据的。“诸侯有顶牛者”是说穆王时的事情。按照“礼乐征伐自皇帝出”的周代轨制,诸侯之间的矛盾一律由王室出头赓续。此时为了赓续诸侯之间的矛盾而专门制定了一套刑法,可见这种“顶牛”仍是是十分严重的盛大景色了。这也阐述王室对诸侯的驱散力大打扣头了。这种景色到了懿、夷二王时仍是更加严重了。《诗谱序》说: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烹皆哀公,夷身失仪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犹衰,周室大坏。 对于烹皆哀公一事,史书多有记录,但稍有不同。《古本竹书编年》言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皆哀公于鼎。”[7]莫得说原因,而且记到夷王头上。《公羊传·庄公四年》说:“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8]讲了原因,却莫得指明是懿王照旧夷王。《史记》之《周本纪》不记其事;《皆世家》则说:“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记事更详,但同样莫得阐述谁为烹东说念主者。从这里的叙事口吻可以看出,这位烹皆哀公的东说念主有可能是夷王,也有可能是夷王之前的孝王,天然还有可能是孝王前的懿王。上引郑玄是明确指出为懿王所为的。总之是懿夷二王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阐述,周王室仍是依靠凶狠刑罚夷戮来保管其巨擘了,这小数与周初诸王频繁辅导我方悉力幸免的殷纣之所为终点接近了。是以可以说从这个时期启动,西周启动走向让步了。于是“礼崩乐坏”的迹象也启动线路: 《礼记·郊特牲》:“觐礼,皇帝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皇帝之失仪也。由夷王以下。” 《史记·卫世家》:“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 夷王为何下堂而见诸侯?不知所以,总之是失仪之举。卫君本为伯爵,竟然可以因行贿而升为侯爵,可见夷王我方对先人传下来的礼法毅力不放在眼里了。以“德治”为基本精神的礼乐轨制本来是要东说念主们自觉信奉的,倘若东说念主们失去了对它的结拜性、巨擘性的自觉招供,这种轨制的敛迹力也就不存在了。礼乐轨制是一个严实的范例系统,只须有一个门径被禁闭,那就会速即发生四百四病。西周后期的情形恰是如斯。又因为西周的政治轨制与价值不雅念体系是相亲相爱的,因而轨制的禁闭也就意味着价值不雅念体系的禁闭,于是西周这个宏大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就必不可免地陷于错落之中了。 恰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诗东说念主启动“作刺”了: 懿王立,王室遂衰,诗东说念主作刺。(《史记·周本纪》)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史记·楚世家》) 周说念始缺,怨刺之诗起。(《汉书·礼乐志》) 至于王说念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序》)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烹皆哀公。夷身失仪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犹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牢》、《板》、《荡》勃而俱作。众国纷然,怨刺相寻。(《诗谱序》) 咱们莫得意义不信托这些记录。关联词咱们可以追问:尽管懿王以降,周室由衰微而至于大坏是历史的事实,关联词这也并不是产生怨刺之诗的充分条目呀!东说念主们抒发不悦与大怒的方法多得很,为什么众人不谋而合地接纳诗的方法呢?对于这个问题咱们照旧要从诗之功能演变的角度往还应。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特定的言说方法。东说念主们为什么聘请这种方法而不聘请另外的方法,源流取决于先在的文化资源——东说念主们老是在前东说念主提供的言说方法的基础上来言说的。对于西周后期那些领有言说才气的东说念主来说,“诗”无疑是他们最粗拙、最灵验的言说方法。缘何见得呢?这与周东说念主的文化汲引径直相关。照旧让咱们先来看史料。 《周礼·大司徒》: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 、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大司乐》: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开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说念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说念、讽、颂、言、语。以乐舞教国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来宾,以悦远东说念主,以作动物。 《礼记·王制》: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学记》: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可安弦。不学博依,不可安诗。不学杂服,不可安礼。 《内则》: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国语·楚语上》: 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险阻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从西周乃至春秋时期的贵族汲引是十分发达的。这是势必之事,因为西周统帅的政治架构是封建宗法制,其维系这种政治架构的主要方法是礼乐文化和每个个体的说念德自律。这么西周的的文化汲引就具有径直的政治意旨,汲引作为一种最垂危的“意志形态国度机器”就是好意思满存效统帅的最主要的方法。就其汲引内容来说,礼、乐、射、御、跳舞等都是具体的典礼,具有物资性,在翰墨书写方面则只须诗、书。而且这些都是十三岁收小学时就启动学习的主要内容。这么汲引的驱散是每一个受汲引者都多艺多才——忽闪音乐、跳舞、诗歌、政治、历史、射箭、驾车以及多样场合的全副礼节。这是确实的贵族汲引,培养出的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东说念主才。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可以说涓滴不假。这小数咱们从《左传》、《国语》这类历来以为很可靠的史书中就可以得到印证:春秋时期各国的那些卿医师,包括军当事人座,哪一个不是文质彬彬?即使敌国间干戈也显得极有法则,更不必说酬酢场合的委婉辞令了。如果将春秋时期贵族们的行事方法、音容笑颜与战国时期那些狗盗鸡鸣、惟利是图者比拟一下,果真有着一丈差九尺!按说春秋与战国邻接,风气之变也就是百十年的事情,这变化缘何如斯之快呢?要害在于春秋时期周王室天然仍是衰微,寰宇只须在那些强劲诸侯的号令下才能造成一刹的一致性,关联词西周的那套礼节轨制和汲引轨制并莫得消释,非常是贵族阶级依然是社会的主导力量,故而除了在礼节的使用纪律上出现了紊乱情形以外,礼乐文化尚莫得消一火,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因此春秋时期贵族们的彬彬有礼经常为后东说念主称说念。钱穆先生尝言: 大体言之,那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因此他们对东说念主生,亦有一种澄澈而稳健的看法。那时的海外间虽则赓续以火器相遇,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酬酢上的素雅风致,更足泄漏那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斗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东说念主说念、讲礼貌、守信让之造就,而有时则成为一种那时额外的幽默。说念义礼信,在那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各国贵族阶级……他们识见之豪阔,东说念主格之完备,瑰意琦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春秋期间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达到一种极优好意思、极崇高、极精细精良的期间。[9]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仍是走向没落,然在文化上还有如斯的泄漏,由此可以想见西周隆盛时期之贵族文化是多么灿烂光泽。 诗歌在西玉成春秋贵族文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垂危地位。启动时在官方汲引系统中传授诗歌的主要筹备毫无疑问是为了礼节轨制能够得到胜仗的实行,因为诗与乐、舞相相关,是礼节中不可枯竭的构成部分。但同期也包含着说念德的、政治的筹备。这种汲引的驱散使得每一位受汲引者都对那些插足官方文化系统的诗歌极为闇练,致使东说念主东说念主可以诵之于口。春秋时贵族们的随口引诗、赋诗就足以证明这小数。如斯,则为东说念主们利用诗这种额外的言说方法来抒发意见提供了可能性。 也就是说,西周懿夷二王之后日渐陵迟的历史语境为“诗东说念主作刺”提供了社会需乞降主不雅动机;西周以来的礼节轨制和汲引所造成的贵族们东说念主东说念主熟知诗笙歌舞的文化语境为“诗东说念主作刺”提供了言说方法上的可能性,于是以怨刺讽谏为主导的诗歌创作便蔚然成风。关联词这里还有一个莫得赓续的问题:履行成果。包括日常活命的往来之内的任何一种言说都要有听者,否则就弥散不会获取盛大的体式。而且这种言说还须通过听者而产生一定的效应,否则也就难以历久存在。对于西周后期那些被称为“变风”、“变雅”的诗歌来说,这个灵验性原则亦然得当的。就是说,除了上述历史文化语境所提供的可能性以外,诗歌功能的根人道变化还肯定有某种机会作为动因。那么,什么因素充任了这种要害动因呢?我以为应该是采诗、献诗的官方行动。 三 咱们前边仍是谈到,对于采诗、献诗问题是清代以来《诗经》商酌领域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有些学者以为西周期间确有这么一种轨制,有的学者则以为是汉东说念主的逸想化说法,并莫得履行存在过。对于采诗之说自清代以来多有疑者,其中最有代表性、质疑也最为有劲的是清东说念主崔述,他说: 旧说,周太史掌采各国之风。今自《邶》、《鄘》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缘何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缘何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曰:孔子之所删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必,诸侯贤者必多;其民岂无称功颂德之词?何为尽删其盛,而肚存其衰?……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后之诗居其泰半;而《春秋》之策,王东说念主至鲁,虽寒微无不书者。缘何毫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于后东说念主揣摸无疑也。盖凡文章一说念,好意思斯爱,爱斯传,乃寰宇之常理;故有作家,即有传者……否则两汉、六朝、唐宋以来,并无采风太史,缘何其诗亦传于后世也?[10] 崔述是清代知名学者,以善于怀疑古东说念主成说著称,其《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都是为东说念主称说念的好书。关联词这里对“采诗”之说的怀疑却是站不住脚的。对于他的质疑咱们可以作念如下讲解: 第一、对于采风前少后多的问题。当代以来的学界早已达成共鸣:“二南”《豳风》等许多旧说以为是西周之初的作品其实大都是西周之末到春秋时期的作品。这么一来,可以以为是周初之作的风诗就历历了。即使有之,也并非从民间集聚而来,举例《鸱鸮》、《七月》之类。咱们证据诗歌在西周时期的功能判断,周初乃至西周中期昔时的确并不存在“采诗”之事。因为那时的封建宗法轨制与礼乐轨制都得到严格的谨守,王室并不需要通过采诗不雅风这么的举措来了解什么。如果从周初即有采诗之制,那么即使五年从一国采得一首,那数百年间、数百国中也应罕有万首之多了。这些诗都到那边去了呢?唯独合理的解释是西周中世之前并莫得采诗之制。关联词这并不等于西周就根底儿莫得采诗之事。倘若无东说念主集聚,《国风》之诗遍于寰宇,是如何被集为一编的呢?由于风诗绝大多数都产生于西周之末和春秋前半期,是以咱们有益义以为采诗的事情是发生在西周中世之后。至于为什么采诗,大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确如汉儒所言,是为了不雅俗例。昭穆二王之后,周室渐衰,王室间有失仪之事,诸侯亦始有不敬之举,诸侯之间更是矛盾缓缓强烈,出现了私自相互攻伐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王室为了加强驱散,以保管王室的统帅地位,于是想出采诗不雅风的办法,以此作为对诸侯接纳褒奖与处分的依据,或者通过风谣了解诸侯的动向,客不雅上亦然对诸侯们一种监督与警示。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看厉王、幽王之所为未必会有这么的政治襟怀。采诗的另外一种更加着实的原因则是王室和贵族们文娱的需要。歌舞乐章尽管是作为绝顶庄严肃肃致使具有结拜性的的礼节的构成部分而插足官方文化系统的,关联词它们从一启动就包含着审好意思的价值,这是进攻置疑的——天下上任何一种宗教性的乐舞绘图等艺术体式无不具有审好意思品质,宗教借助于艺术宣扬自身的同期,艺术也削弱了宗教性自身[11]。如斯久而久之,贵族们被礼节的乐舞培养起来的审好意思需求天然会缓缓增强,不免对原有的、老旧的乐舞渐生讨厌,于是就但愿有新的东西来餍足审好意思的需要,这么就有了采风的事情发生——名山大川的声调各有不同,适值可以餍足众人的口味。如斯则诗是借了乐调的光才得以插足王室贵族文化之中的。 对于这小数,大略可以从“无算乐”的用途中看出来。在《仪礼》之《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等篇,均有“无算爵”、“无算乐”之谓。郑玄注“无算爵”云:“算,数也。宾主燕饮,爵行无数,醉而止也。”注“无算乐”云:“燕乐亦无数,或间或合,尽欢而止也。”[12]盖于“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等礼节的崇拜节目中,饮酒次数与用乐数均有严格端正,不可有涓滴差错。关联词在崇拜节目之后,则可以尽情饮酒、尽情用乐,此所谓“无算”。何定生先生以为“变风”、“变雅”之作基本上都是用之于这种“无算乐”的。其云: ……且(燕礼和乡礼)于诸礼之中,用诗最多,犹以“无算乐”之用为最经常而垂危,包括了绝大多数小雅和简直全部的国风诗篇。这是个相等垂危的趋向。这个趋向可以阐述周乐一面是由王乐的严肃而趋向于乡乐的减轻,另一面则三百篇之用,也由于正歌正乐而趋向于散歌百戏。[13] 是以他以为所谓“变风”、“变雅”就是指在作为乐章的使用上不同于以往那些“正歌”、“正乐”的作品。这是很有观点的说法。何先生所说的这种趋向应该是西周中世之后才启动的,这也恰是崔述所不明的采诗之“前少后多”的原因处所。用于纯正的审好意思文娱筹备的诗乐除了所谓“无算乐”以外,《仪礼》又有“房中之乐”说。郑玄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必钟磬之节也。谓之‘房中’者,后夫东说念主之所讽谕以事正人。”[14]清东说念主阎若琚以为:“今不雅之二南……信其为房中之乐也。”[15]《毛传》亦以为《正人阳阳》等诗为“房中之乐”[16]。可见《诗经》中确有许多作品是作为“房中之乐”来使用的。尽管古东说念主以为这类诗歌也有劝戒讽谕之用,但在咱们看来,其主要用途亦与“无算乐”一样肯定是审好意思文娱方面的。 那么这些用于审好意思文娱需要的诗歌从何而来呢?大要一部分是命周王室径直驱散地区的医师士或乐师、乐师们专门制作的,而更多的则是命东说念主到各国采来的。由此咱们有益义以为,“采诗”其实并不是一种轨制,而是证据需要临时接纳的门径。很可能是王室为了保持尊荣,将这种“采诗”行动结拜化,打出“采诗不雅风”的旗子。是以,采诗的事情肯定发生过,但不大可能是周初就有的定制。对于这小数古东说念主亦曾有所触及,咱们看底下一段话: 或曰:先儒多以周说念衰,诗东说念主本诸衽席而《关雎》作。故扬雄以周康之时《关雎》作为伤乱始。杜钦亦曰:“佩玉晏鸣,《关雎》谈之。”说者以为古者后夫东说念主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否则,故诗东说念主叹而伤之。此鲁说也,与毛异矣。但以“哀感顽艳”之意推之,恐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仪礼》以《关雎》为乡乐,又为房中之乐,则是周公制作之时已有此诗矣。若如鲁说,则《仪礼》不得为周公之书。《仪礼》不为周公之书则周之盛时乃无乡乐燕饮、房中之乐,而必有待于后世之刺诗也。其否则也明矣。[17] 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恰是朱熹所商酌的这种不雅点是合乎履行的。这种不雅点是从鲁诗的逻辑推出来的。宋儒服气《仪礼》为古“礼经”,是周公所作无疑,故有此辨说。当代以来,学界对于《仪礼》的商酌早已证明其为战国乃至西汉儒者证据留存的一些古代文件写定的,决非周公所作。证据“采诗”及“变风”、“变雅”之原始功用的辨析,咱们可以说:周公制礼作乐之时的确莫得大范畴使用“无算乐”、“房中之乐”的情况。这些乐歌乃是西周后期才经常插足贵族们的文化活命的。“采诗”之举的产生与这种主要用之于审好意思文娱的乐歌有径直的揣度,是其主要动因。 第二、对于删盛存衰的问题。如前所述,周初那些作为乐章的诗歌都是定作的,即为了礼乐典礼的需要而专门作出来的,并非东说念主们自愿地鼓掌称快之举。礼乐轨制一朝详情,何礼用何乐都成定制,后世沿用即可,不必再有新的创制。是以《诗经》中的颂好意思之作东若是向着文王、武王和周公的也就不及为奇了。盛世之诗本来就少,衰世之诗本来就多,这是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所导致的诗歌功能之演变的驱散,根底儿就不存在什么删盛存衰的问题。 第三、对于《左传》不载采诗之事的问题。有了上头的阐发,这个问题也就不难回应了:采诗从来不是一件垂危的政治门径,而主若是为了王室贵族们的文娱。而且这种事也从来都莫得造成轨制,只是偶一为之的事。是以采诗之事不入于史官的视线亦然极有可能的事情。尽管如斯,在先秦典籍中照旧可以看出相关的记录的。为了粗拙起见,这里引一段一位后生学者的叙述: 古有所谓“王官采诗”说,前东说念主多不之信,原因是相关此说的记录都是汉代的。战国竹简《孔子诗论》的再世,有劲地证明了汉儒说是有证据的。《诗论》第三简说:“邦风其纳物也博,不雅东说念主俗焉,大敛材焉。”“邦风”可以“不雅东说念主俗”,也就是典籍所记“采诗不雅风”的“不雅风”,而“王官采诗”的“王官”一义,则含在“大敛材”一语之中。“敛材”,马承源先生的考释是:“指(汇集)邦风佳作,实为采风。”[18] 对于“敛材”一语,王志平先生以为应读为“敛采”,就是“采诗不雅风”的真义[19]。如果马承源、王志平、李山等贯通的可以,那么周东说念主有采诗之事就更加着实无疑了。只是儒家对此事的贯通似乎带有逸想主见色调,正如他们对西周的许多事情的贯通都带有逸想化因素一样——他们经常把本来莫得什么政治意旨的事件叙述为饱含深意,这是儒家语言建构的基本计谋之一,不及为怪。是以周王室的采诗未必真的是为了“不雅东说念主俗焉”。 咱们详情了采诗之事的履行面容以后,对于民歌民谣与政治色调极浓的讽谕怨刺之诗简直同期“勃尔俱作”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各地的民歌都有我方的特色,汇集这些民间作品稍加校阅,就可以成为具有不同风范的歌曲而供王室和贵族们赏玩。对于这小数,我不可本旨许多知名学者举例朱东润、钱穆以实时下一些论者含糊《诗经》中有民间作品的不雅点。他们以为这三百零五篇诗歌都是贵族制作的,这是不合乎履行的。《诗经》中有些精练欢乐的作品飘溢着民间气味,弥散不可能是贵族们闭门觅句的产品。但我信托这类民歌汇集到之后在某些词语、韵律方面经过了贵族们的润色。这是“无算乐”和“房中之乐”的开始之一,天然亦然《国风》的主要开始之一。这类从民间采来的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自身毫无政治内涵,纯正是无邪烂漫的情歌或管事之歌,举例《静女》、《桑中》、《褰裳》、《七月》之类,此类作品的创作完全是自愿的,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产品。另一类是各地庶民调侃当地诸侯或仕宦或者士东说念主、医师之间相互讥诮的,举例《伐檀》、《硕鼠》、《新台》、《相鼠》之类,这类作品的创作很可能恰是受了王室采诗的引发才忻悦起来的。作诗者的筹备是借采诗的机会向王室诉说我方的愤慨与扞拒。关联词这些作品亦与其他民歌一样,均因其音调而得以裁剪、流传,周王室并不一定真的讲理其辞旨,只是赏玩其乐调。 《诗经》中最令东说念主困惑的是“变雅”中那些被《诗序》、《郑笺》以为是调侃周王的作品。举例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等,小雅中的《祈父》、《白驹》、《黄鸟》、我行其野》、《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以下,不是刺宣王就是刺厉王、幽王。我并不含糊这些作品都是满腔忧愤的宣泄,都含有讥诮和怨愤之情,但令东说念主难以索解的是:这类作品缘何能为王室所遴选并比其音律,赞颂于大庭广众之下呢?难说念周王室虽已让步,但如斯优容的襟怀却还在吗?咱们看《国语·周语》中厉王那种“弭谤”的期间,是多么狠毒!他如何能够隐忍国东说念主、士、医师们用这么的诗来调侃他呢?即使可以隐忍,又如何将其汇集编著、传诸后世,以遗万世之羞呢?故而咱们只可说《诗序》、《郑笺》将这些诗定为“变雅”,以为是“刺诗”大体上是莫得问题的,但指实某诗刺某王的说法是莫得证据的。这也恰是历代怀疑毛郑诗学的东说念主所共有的不雅点。我的贯通是,这类作品都是在王室的号令之下写出来的,在王室一面大要是为了补充“无算乐”、“房中之乐”之用,在作诗者的一面却是要借此机会抒发我方的怨愤扞拒之情。于是咱们就势必触及到“献诗”的问题了。对于这方面的主要记录如下: 《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语: 故皇帝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尔后王揣度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晋语六》载范文子语: 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也……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子革与楚王语: 子革对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寰宇,将皆必有车尘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招德音。念念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愔看这几笔记录咱们知说念,献诗天然不是厉王、幽王和春秋时履行存在的事情,但在昔时的某个时期大要的确存在过。那么那些被毛诗以为是刺宣王、厉王、幽王的“变雅”之作究竟是何时之诗呢? 咱们以为,这些诗篇中除了《六月》等几首容貌开采的大致可以以为是宣王时所作以外,其他的基本上均很难详情其产生的确切期间,也莫得充分的意义以为它们就是讥诮谁东说念主、惊羡谁东说念主。但有小数是可以肯定的:这些诗都是专门作了献上去的[20]。其产生的期间则是西周中世直至平王东迁前后[21]。以往论者检修作诗的年代都将重目力蚁合在期间的政治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创作冲动上,这天然是可以的,关联词这些还不是充分条目,因为倘若莫得适当的文化语境,东说念主们是不会用诗的方法来抒发扞拒之情的。在我看来情况应该是这么的:从西周中世启动出现了采诗之事,筹备是为王室和贵族们用于“无算乐”或“房中之乐”等文娱。追随采诗行为的就是献诗,王室饱读吹公卿列士献诗,用途与于民间采诗同。关联词这些不但有文化造就而且有政治不雅点的卿医师士们并不宁愿只是为王室提供文娱之资,于是他们就借着这个献诗的机会来抒发我方的政治作风以及对于现实的看法。于是就产生这些了“变雅”之作。因此这类作品中有写征伐的,如《六月》、《采芑》等,有惊羡皇帝的,如《吉日》、《云汉》之类,但更多的却是抒发哀怨、愤慨与调侃之作。诗东说念主们完全是按照我方的意愿作这些诗,是属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这与周初那些为了建构意志形态而定作的“颂”诗及“正风”、“正雅”有着根本的不同。诗东说念主发泄情感的目确天然是要引起当政者的防卫,从而改变诗东说念主我方的不利地位或境遇。关联词这类诗履行上并莫得起到这么的作用——它们被太师或史官们作了翰墨上的加工,又被乐师们谱了曲,然后就是扮演于多样人人的或私东说念主的时势,成为一种纯正的艺术品了。 如斯看来,《诗经》作品从颂诗、正风、正雅到变风、变雅的转化本色上乃是诗歌功能的退换——由崇拜礼节中的“正歌”、“正乐”到礼节之余的“散歌”、“百戏”的退换,而这种退换又引起了从代表集体意志或情感的定作之诗到泄漏个情面感的解放创作的退换,或者说是从作为礼节轨制之构成部分的乐章向私东说念主化言说的退换。如果从言说的对象来看,则前者主若是由上而下的,即王室对包括诸侯在内的臣子庶民的造就,后者却主若是由下而上的,即国东说念主、公卿医师们对王室的讽谏。从意志形态意旨的角度看,前者代表了国度主流语言,是纯正官方性质的,后者代表了国民的盛大心情,是民间性质的。这种退换天然依赖于社会政治现象的改变,即依赖于封建宗法制的松动与相应的礼法的缓缓毒害,还要依赖于彼时发达的贵族汲引与国民汲引,使“诗”这种东西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言说方法。关联词最径直的机会却是王室的采诗之举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献诗之举。献诗乃是采诗的追随物,周王室的初志很可能是出于文娱的筹备,但驱散却是引发了东说念主们用诗来抒发个东说念主语言的高潮。由于诗不管如何是一种委婉的、间接的言说方法,是以其贮蓄的政治性被其体式淡化了,再加上动东说念主心弦的乐调,听者就比拟容易遴选其中的政治含义而不至于反感,这也许就是《诗大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的功能了。这么一来,“变风”、“变雅”也就真的成为从下到上的疏导方法,真恰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了。 终末咱们还有必要对“谁在言说”这个话题作念一些进一步的念念考。从诗的文本来看,“变雅”的作家主若是公卿医师是无疑的,对此可以不必置论。那么“变风”的作家主若是什么东说念主呢?从相关的文件记录来看,“变风”的作家主若是“国东说念主”。从《左传》、《国语》等文件中咱们可以知说念,所谓“国东说念主”实在是一个很有政治力量的阶级。他们似乎对国度事物十分讲理,何况可以通过多样方法干扰或参与政治方案。让咱们看《左传》所载的几则事例: 僖公二十八年:为了抗衡楚国,晋与皆在敛盂会盟,卫国也想参加,晋国不本旨。卫侯一气之下决定与楚国缔盟,驱散遭到“国东说念主”的反对,将卫侯斥逐了。 文公十六年:宋国的令郎鲍对“国东说念主”极为谦敬有礼,饥馑时又拿落发中全部食粮来拯救他们。对于年岁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东说念主还有非常的送礼。对于有才干的东说念主则尤其殷勤有加。那时的国君昭公无说念,“国东说念主”就一齐拥护令郎鲍。驱散昭公陷于孤独孤身一人,终末被东说念主杀死了。 文公十八年:莒纪公可爱小女儿季佗,于是废了太子仆,还在国内作念了许多荒唐悖礼之事。于是太子仆就依靠“国东说念主”的赈济杀了纪公,带了大都珠宝跑到鲁国去了。 成公十三年:曹国的令郎欣时很得民意,他对曹国国君成公不悦,商酌离开曹国到别的国度去,驱散“国东说念主”知说念了这个音书,都要和他一齐走。成公这才感到问题严重,向令郎欣时和“国东说念主”承认我方的漏洞,肯求他留住来。 从这些事例上看,春秋时期“国东说念主”可以说是一个诸侯国的基本力量,谁得到他们的赈济,谁就可以得到奏效。即使是国君,如果失去了“国东说念主”的信任,也就失去了统帅的正当性,很快就会失位了。“国东说念主”之是以有如斯强劲的力量,主若是因为他们履行上是一个诸侯国的撑持:他们是国度队列的主要开始,是国度经济的基础,而且照旧社会公论的主导者——他们弥散不是只是可以干戈和出产的管事者。证据相关史料可知,“国东说念主”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汲引的国民[22],因此他们对于诗书礼乐都很闇练。恰是这后小数使得“国东说念主”也能够成为那些政治调侃诗的作家。他们经常用诗歌的方法来抒发我方对时政的看法。《左传》隐公三年载:“卫庄公娶于皆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好意思而无子,卫东说念主所为赋《硕东说念主》也。”又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东说念主哀之,为之赋《黄鸟》。”那些“变风”之作,肯定有许多是这么的作品,只是史家无暇逐个记录而已。咱们看对于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政治事件的记录,遍地可见对于“民”的疼爱,在我看来这个“民”决不像后世某些时候只是是一个缺乏的倡导,代表的履行上乃是自称为为民者自身的利益,而是实有所指:就是那些可以发表意见并有履行的政治职权、非常是可以掌捏公论的“国东说念主”。由于“国东说念主”与诸侯国的举座利益喜忧与共,是以都具有很强的爱国精神,对于那些危害国度利益的东说念主和事他们都会以多样方法抒发我方的不悦,致使接纳暴力期间。除了有时也有被表层贵族利用从而卷入权力斗争的情形以外,“国东说念主”基本上可以代表对于国度举座利益来说是“正义”的声息。由于“国东说念主”中那些优秀分子或代表东说念主物遴选过正规汲引,对于西周以来的那套礼乐文化十分闇练,是以他们就能够用诗歌这种特殊的言说方法来抒发对于帝王、卿医师以及国度大事的作风和意见。春秋时期国是侵略、社会原有纪律受到冲击,“国东说念主”的活命也变生不测,于是引发起他们借诗歌来怨刺、讽谏的热沈,这就造成了“变风”的勃兴[23]。这种情形与两周之交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受到冲击,致使不少贵族沦为遗民,从而导致“变雅”之作的忻悦是同样的道理。可惜的是,这些诗天然被王室集聚、编著、并入乐,关联词却弥散莫得确实瓦解箴谏劝戒的政治作用,其驱散,从永久的文化史发展看,是为后世留住一部记录了公元前六七百年前东说念主们喜怒无常并具有极高文体价值的伟大作品,而从较近的社会文化现象看,则是为贵族阶级提供了一种素雅的、身份性的额外言说方法——这在春秋时期的“赋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 最近亦有论者以为《周颂》之《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四首乃专为穆王继位典礼而作。(见马银琴《西周穆王期间的典礼乐歌》,赵敏俐主编《中国诗歌商酌》第一辑,第3-28页。)可备参考。我以为,此期大略会有个别诗歌的创作,举例时王对父祖进行祭祀时用之,但不可能有大范畴的诗歌创作。郑玄并非松驰言之的。 [2]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见《古史辨》第三册下编,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影印本,第654页 [3] 何定生:《诗经今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251页。 3 参阅清东说念主崔述《读风偶识》、魏源《古诗微》等 4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书社1996年三月版,第69页。 5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三,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8页。 6 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三引,岳麓书社标点本,第78-79页 1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引,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三,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9页 2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三,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0页 3 转引自蒋伯潜、蒋祖怡著《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书社,1997年版,第43页。 [5] 钱穆:《读诗经》,见中国粹术念念想史论丛》(一),台湾东大文籍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20页。 [6] 《古本竹书编年·周·康王》,见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编年辑校》,辽宁汲引出书社校点本,1997年版,第12页。 [7] 《古本竹书编年·周·夷王》,见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编年辑校》,辽宁汲引出书社校点本,1997年版,第15页。 [8] 《新刊四书五经·春秋三传》,中国书店标点本,1992年版,第95页 [9]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1页。 [10] 崔述:《读风偶识》卷二,《通论十三国风》 [11]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对于玄学校阅的临时提纲》一文中谈到基督教艺术时指出:“基督教徒只须履行上含糊了基督教神学,将女性的本色行为结拜的本色加以进展时,才走向诗歌,当基督教徒对宗教的本色进行假想时,当宗教的本色成为他们的意志对象时,他们就与他们的宗教的本色发生了矛盾,成为艺术家和诗东说念主”。(见《费尔巴哈玄学著述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5页。)这里费尔巴哈是要阐述艺术与宗教本色上的对立,但也阐述了即使是宗教艺术,也照旧保留了艺术的品质。宗教试图利用艺术为我方服务时,履行上反而被艺术削弱了其宗教性。 [12] 《仪礼注疏》卷四 [13] 何定生:《诗经今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068年版,第8页。 [14] 《仪礼注疏》卷六 [15] 阎若琚:《尚书古文疏正》卷五下 [16] 《毛诗注疏》卷六 [17] 朱熹:《诗序辨说》卷上 [18] 李山:《举贱民而蠲之》,见所著《诗经析读》,海南出书公司,2003年版,附录二 [19] 王志平:《诗论笺疏》,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商酌》,上海书店出书社,2002年版,第211页 [20] 顾颉刚先生尝说:“公卿列士的讽谏是特意作念了献上去的,庶东说念主的月旦是给仕宦探访到了告诵上去的。”又说“就怕这种事(指献诗——引者)在春秋前许多,在春秋时就很少了……可见东周时这类的风气还莫得歇绝。但这类的诗都在大小雅中,大小雅是王朝的诗,或者献诗诵谏的事是王朝所额外也未可知。《左传》既不防卫王朝,天然莫得这类的记录。”(见《古史辨》第三册下,北京书局《民国丛书》本,第326—328页。) [21] 李山的近著《诗经析读》(南海出书公司2003年3月版)以为“幽王及新立太子伯盘身后,西周朝廷并未速即沦陷,大臣虢公翰曾立余臣为继世周王,从而造成‘二王独立的历史局面。直到晋文公二十一年、携王在位十余年之后,这局面才告终端,平王方始东迁。十余年的时刻天然只是历史的刹那,但对诗歌创作而言,却足以助长一个独具色调的文体期间。大、小雅中深远充满哀怨与愤心心情的政治抒怀诗,就大多产生于这么一个十年内。”(《节南山》析读)这是一个很斗胆也很有新意的不雅点,可备参考。 [22]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医师、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所谓“国之俊选”即是指那些“国东说念主”子弟中蛟龙得水者。《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周东说念主对于“国东说念主”的汲引的确是十分疼爱的,这天然与其对礼乐轨制的履行与保重径直相关。 [23] 这里主要指“变风”中那些怨愤之作而言。至于那些容貌情爱与劳顿的作品则很可能是民间永远流传的诗歌,其产生年代是不可知的。
情色电影bt